一辈子靠吃药和抑郁抗衡,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What It's Like To Be
On Antidepressants Long-Term
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
壹心理翻译社 ◎ 荣誉出品
原作 | Danielle Tcholakian
翻译 | 搬那度
校编 | 张真Derek
写在前面的话 >>
今天为大家呈现的这篇文章,是一位抑郁症患者的自述。
从 “一辈子都要服药、仿佛被判无期徒刑” 的无助和绝望,到试图停药后病情的反复、失控,再到后来重新认识药物、也拥抱自己……
朴实无华的文字背后,是痛苦的挣扎,是希望的光亮,更是抑郁症患者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除了书写自己的故事,作者也结合社会现象和心理学对抑郁症的专业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精神药物” 对患者而言,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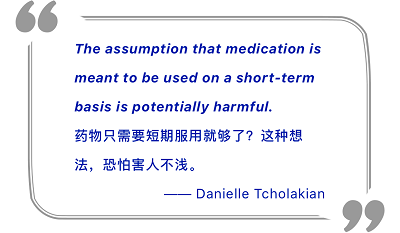
- 01 -
“医生,这药,我是不是得吃一辈子?”
几年前,我问了医生:“我想尝试把其中一种药停掉,可以吗?”
我患有抑郁症,当时的我,服用同一个药物疗程已有数年。我那时吃的药有三种,总觉得吃那么多药其实不太好。
她问:“药是不是产生了副作用?还是你觉得药没有效?”
我说:“不是,不过我有去运动,胃口还不错,人也觉得蛮好的,所以应该是治好了吧!”
最后,我们互相让了步,把其中一种药的量稍微减少了。

然而两个月后,我却哭着回到了她的诊所。不知道为什么,原本一切都好好的,现在情绪却一团糟。
她问:“你这样子的感觉已经有多久了?”
我说:“可能有大概一个月吧。”
她指出,在我情绪开始变糟的不久之前,我们才刚把其中一种药的量减少。
听罢,我大笑了起来 —— 哈哈哈,问题有了解决方法,我可以放心了!
不过我又问了她:“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要吃药?”
我还记得,她很谨慎地看着我,然后问道:“这个想法是不是让你难受?”
“没错。” 我回答得很干脆。
“为什么呢?”
我一下子回答不上来。也许是钱的问题吧?讨厌的是,维持我的生命,居然比维持 “正常” 人的生命还要贵。
她点了点头说道:“这点我完全理解。不过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我思索了许久,最终说道:“可能是惭愧吧?是不是我太软弱所以觉得惭愧?”
她问了我:“你觉得其他吃药的人都是软弱的吗?”
我立刻摇了摇头 —— 当然不是!
她反问道:“既然这样,你又怎么会觉得自己软弱呢?”

- 02 -
社会对抑郁症药物的 “污名化”
有人说,吃精神疾病药的人是软弱的。这个想法背后,似乎是内化的社会污名(social stigma)在作祟。
奇怪的是,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想法还是有分歧的:很多人似乎认为,精神疾病不如所谓的 “身体疾病” 来得 “真实”。
但是,难道大脑就不属于身体的一部分吗?
一个人一旦患上精神疾病,可能就无法起床,连走一小段路也做不到,吃饭又吃不好 —— 这怎么可能不是身体疾病呢?
这种观念背后的假设就是:看不见的痛苦是不真实的。
最近,《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被广泛分享的文章,标题为《许多服抗抑郁药的人发现自己戒不了药》。文章的潜台词正是:“看不见 = 不真实”。
对许多人来说,抑郁症是慢性疾病。(研究人员在201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抑郁症会复发,而且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往后还会患上慢性抑郁症。”)
但是,文章隐含的假设似乎却是:长期吃药,本身就是个问题。
更糟的是,这篇文章完全忽略了以下几点:
停止服药是抑郁症患者的一个常见死因;
许多人一旦情绪开始变好,就会忘了之前觉得有多糟糕,忘了自己之所以情绪变好是因为之前吃了药,于是就不再吃药;
对许多人来说,不吃抗抑郁药或者抗焦虑药,虽然能避免产生副作用和依赖性,但是换来的却是一种肯定比死亡还糟的感受,甚至是死亡本身。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揭示了精神健康研究目光短浅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真实,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也曾在 2010 年探讨过。
事实上,精神疾病相关的研究,时间和金钱成本都很昂贵,这不符合制药商追求的利益目标。而且,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由制药商出资进行的,就连在学术机构进行的研究也不例外。
可是事实不仅如此:大脑是人体中最复杂的器官,所以我们对大脑的理解仍处在初期阶段(就像伽利略对宇宙的初期理解一样)。
人们把精神疾病当作医学问题来进行认真研究,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还有很多知识是医生和研究人员还没发现的。
我们甚至都不确定问题一定是出自大脑,而非出自中枢神经系统的另一个部位,甚至完全不同的系统。举个例子:2015 年的一项研究指出,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可能就是我们对抑郁症的理解中 “所缺少的环节”。
有些人确实可以只服用短期的抗抑郁药或抗焦虑药。而且令人沮丧的是,在这些人服用的药物中、停用后不会造成问题的也只有几种而已。
然而,许多人必须无限期地服药。所以,要是以为 “药物只需要短期服用就够了”,恐怕害人不浅:这种想法不但会助长污名化,还会让 “吃药等于软弱” 的想法经久不散。
比如,《纽约时报》那篇文章中就有这么一段话:“长期服药者在访谈中表示,一种难以衡量的不安情绪会逐渐降临:他们说,每天服药的行为,导致他们质疑自己的韧性。”
这不就是社会污名的后果吗?污名,让很多人的心态变成了:对自己的病情负责,非但不是坚强或智慧的表现,反而却是缺乏 “韧性” 的迹象。
人为什么对痛苦有崇拜心理呢?
痛苦,竟然被赋予了道德价值 —— 难道一个饱受痛苦的人有什么地方是值得赞扬的吗?
用智慧和科学来帮助人们活得更好、更舒适,到底有什么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可以用糖尿病来比喻精神疾病。
注射胰岛素,会不会使糖尿病患者遭到批判?
Maris Kreizman 在一篇发布在 Longreads 网站上的文章中,讲述了她从小患有糖尿病的经历。Kreizman 对上面那个糖尿病的比喻表示支持,她表示:我只有接受了 “自己的糖尿病是终身的” 这个事实,我才能接受:“我的焦虑症也一样,是终身的”。
Kreizman 说:“糖尿病的治愈方法,短期内是不会有的。去年,我发现我的焦虑症也是如此。我之前在发生焦虑危机时,也服用过几次药物。后来我的生活变得非常好,还结了婚,也觉得事业一帆风顺。尽管如此,我还是焦虑得要命。我这才发现,原来我的焦虑症是个慢性疾病,就像我的糖尿病一样。”
有了从小患有慢性疾病的经历,Kreizman 才比较愿意接受长期服药。尽管如此,她还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她患上的精神疾病,和她的糖尿病没两样 —— 两者都是再真实不过的慢性疾病。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小时候没有患上慢性疾病的经历,精神疾病患者就会把服药的行为污名化。

- 03 -
服药,也可以是一种力量
就在我开始接受必须无限期服药的时候,我服用了大概 8 年的药,却失去效用了。
这件事发生在我和精神科医生进行文章开头那段对话的几年后。我在办公室把自己关进了一个空房间里,瘫坐在地板角落,然后给一位最要好的朋友打了电话。
在这之前的几周里,我每天都是一路哭着上班的。
而那一天,我在房间里泣不成声地试着告诉她,我觉得很难受、人生毫无价值、不管我做什么想什么说什么都毫无价值、我非常非常害怕……
她静静地倾听着,又轻声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然后谨慎地说道:“我好久没有听你哭成这样了。”
她这位朋友非常宝贵。像我这样的人,有了这样的朋友才能继续活下去:就算看到了这样的痛苦,她也不会害怕,不会变得不知所措。
那天,她说的一些话,让我回忆起了一件事:
8 年前,我在第二次患上重度抑郁症时告诉了精神科医生,我知道我的感受和想法是其他人不会感同身受的 —— 我当时脑子里尽是:一切都不重要,一切都毫无意义,甚至更糟。
但我就是不明白,别人为什么不能感同身受呢?

精神科医生告诉我:“重度抑郁症会改变大脑的逻辑。一旦复原了,你抑郁时的思维也会变得无法理解。”
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的逻辑已经变了。于是,我打了电话给精神科医生,告诉了她:“我很肯定我的药已经不管用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对药物做了调整。我一边为了生活苦苦挣扎,一边却感觉到自己被什么东西上身,想置我于死地似的。
我试了几种不同的药物。有些药服用之后立刻见效,但过后还是会让我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
或者有些药虽然有效,但是后来却产生了一些副作用,让我难以忍受。
但最糟的是,我觉得很痛苦,别人却完全看不见。
以前,周围的人都不肯承认我生了病,造成了我一度的自我怀疑。我会对自己说:“你不过是软弱罢了,再努力一些吧!”
但实际上,我已经努力到不能再努力了。
而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而做到这些,已经足够。
新的药直到整整两个月后才起了作用。每周,我都会告诉医生:“我感觉没有好转。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觉得好起来?”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更糟。所以,每当她叫我再等一周、再多等一点时间,我都会乖乖听话。
后来有一天,我在市政厅外面走着。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时正逢初春,阳光普照,风清气爽。我刚吃完午餐,正在回去办公室写新闻稿的途中。
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也许我根本就不需要吃这个药,反正我觉得挺正常的,药又没什么效。”
这念头一划过脑海,我就顿住了……
然后,我大声笑了出来。
这个药,有效了。
只是,它的药效很轻微,轻得我甚至都察觉不到。
原来,正确适合的抗抑郁药,才会发挥出如此微妙的效用。

正文部分,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不清楚,写完这篇文章的作者,此时此刻、她和抗抑郁的药物、和抑郁症、和她自己,相处得如何。
我们也不清楚,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在其他抑郁症患者的身上是否同样适用。
我们只知道,作者的文字如此真实。看到末尾的我们,眼睛都是湿润的 —— 那是字里行间透出的理性和温暖,在发光,在闪耀。
衷心祝福 Danielle,也祝福屏幕前每一位受到抑郁和心理困扰的朋友、和你们生命中、那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祝你们安好。
世界和我,爱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