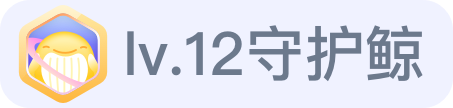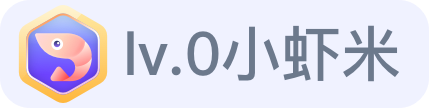每逢过节就拜神的心理是什么?拜神真的有用吗?
 匿名用户
匿名用户#互动反馈
我家是普通的潮汕家庭,每逢过年过节妈妈都会张罗着拜神。
一到过年也会到不同的特定地方拜神,习俗繁杂,但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好多人虔诚地拜神。
我认为“这是个信仰”,但总想不明白拜神到底是个什么心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来拜神?拜神真的有用吗?
9240阅读
·8回答
收藏

这个东西除了宗教信仰之外,更多的是在表达自己可以用“拜神”的方式摆脱“干坏事”带来的负罪感。(非歧视)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鬼神(除了宗教信仰),但即使是作为最坚定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不可避免的牺牲时,也会调侃自己要去见马克思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坚定的无神论,但从业者却不可避免的会将马克思“神化”,这里面表达的既有向死而生的大无畏精神,也有在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心里,通过这种转化,成功的化解了恐惧,因为即使死亡,我的心灵也必将拥抱自己的信仰,回归到那个最伟大的怀抱里。当代人的拜神,甚至包括古代人的拜神与祭祀(其实古代就有很多无神论,子曰: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尽管提倡祭祀,但他的思想却倾向于无神论)代表的都是一种转移内心恐惧,祈求平安幸福的理念。我通过拜神,转移了自己内心的恐惧,那么我还我什么事做不成?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拜神”来达到自我安慰的目的。曾经的香港古惑仔,很多人都会崇拜关二爷,甚至有很多人拜佛,一般在“干事”之前都要拜一拜才觉得心安,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古惑仔要干的“事儿”跟关二爷、佛陀的理念风马牛不相及,但却通过形象化的转移自己的视线(拜佛祈求平安,做法事寻求神灵庇护,强化关二爷的“义盖云天”)使得神灵跟自己站在一起,自己要去做的“事儿”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当然,这里强调的是无关宗教信仰的祭拜,如果是宗教信仰的祭拜就属于《宗教学》,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人,是需要活在当下的,不会活在过去与未来,但是在面对过去时,人可以做总结经验,而对未来就需要展望与祈求,简单来说就是需要幻想,尤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幻想能给当下的人带来巨大的鼓舞与动力。当你感觉到很神灵一体,或者得到了神灵的庇护时,任何现实的困难都会让你觉得不过如此。视死如归不仅仅需要勇气,还需要用幻想转移恐惧。而祭拜的最大作用就在于此。以上只是理性的分析,现实中还是要尊重不同的信仰、风俗、习惯,因为这些东西才是很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理性分析是没有感情色彩的。补充一点关于放生的观点。佛教说“众生平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在面对杀人狂魔时,我们是否也要遵守呢?其实对这类问题的讨论早在两千多面前的战国时代,墨家就做过精彩的辩论,因为墨家思想的核心在“兼爱非攻”,这一点跟佛教思想类似但又不同。简单来说杀人狂魔被杀,其实杀的并不是人,而是魔,人因为有了魔而不再是单纯的人,此时杀魔,杀的就不是人,是魔,因此并不违背“兼爱非攻”的原则。而佛教的“众生平等”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在面对这个情况时就显得有点互相违背,众生平等,杀魔就不是众生平等,不杀魔就做不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然后佛教就创造性的提出了“渡人”的观点,我去掉了这个杀人狂魔的“魔性”,那么他也就不再是“杀人狂魔”,既保留了“众生平等”,有做到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是当代的放生功德,更像是一种商业化的消费,通过花钱来做“放生功德”,通过“消费”来达到“心灵的满足”,完全忽略了放生背后的原则,放生背后的原则是“众生平等”,既然是众生平等又何须依靠你的“放生”来达到“众生平等”?所谓的放生更像是“心安理得”。佛教等宗教注重的是心灵的修养,而非形式上的虔诚,这也是佛教跟伊斯兰教、基督教、古印度教的根本区别,释迦摩尼创立佛教就是看到了苦修达不到净化心灵的效果,希望通过简化清规戒律,使教徒注重心灵的修养,而不是形式上的虔诚。但是,随着佛教的传播,清规戒律与形式上的虔诚又成了主导,不能不说是“舍本逐末”。(后面的说多了)
最早的纸钱,是因为发明纸的人,手上粗糙的囤货卖不出去。于是就有了一个烧路票的『说法』,然后就成了习俗已经某些信仰的变现形式。而实际上,就是一个商业上,成功营销的meme(文化基因)。最近又从『理想国』,梁文道的『八分』里面听到,原来新年去各个庙宇上香,这种我以为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习俗,在日本,仅仅是因为他们全国的铁道建设完成以后,日本人坐的不多。所以,日本人新年上香的习俗是被铁道公司创造出来的,甚至参拜这个词,也是那个时候才被发明的。我们广东人新年,见面就爱讲@恭喜发财@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说,大家都发财是会通货膨胀的!当然,它的心理作用就是放松我们消费时的防御机制。所以我们听到最多的@恭喜发财@肯定是来自于那些想问我们要钱的人,不是商家就是要红包的小孩。当然作为经济推手,要让一种背后隐藏着消费信号的文化基因发展壮大,那比较的作用肯定会一并植入的。我妈拜神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向神明倾诉她的虔诚,同时通过挑剔别人拜神的细节来显现自己的“专业”、权威!反正对于在家里平时地位不高的女性,到了新年拜神的时候,就是她们说了算的时候了!
拜神就和礼仪一样,是心里的向往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比如,高兴了,想唱歌,伤心了想哭。而不是反过来,唱了歌就高兴,哭了就伤心。至于有没有用,如果完全靠出去,就没用。如果只是求神帮助,自己是主力,才有用。至于有没有自我暗示,对于没有把握到精髓的人来说,有。对于把握到精髓的人来说,没有,因为对他们来说,拜或者不拜,是一样的。比如,善卜者不占,如果真的懂了,是不会算的。原因就是,真的懂的,都知道,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真正的佛教徒,心里清清楚楚,如果自己不努力,佛陀都帮不了你。如果你自己努力,他会帮助你,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我的立场,是信儒家的天,道家的道,佛陀说的涅槃,基督教的上帝或者三位一体。但是,我不会刻意拜,因为我的修行,就是每天遇到的任何事情,如果我做好了,不需要拜,如果没做好,拜也没用。为什么要拜,想拜的人,在拜的时候,心里是清明的,温和的,平静的,如果多拜,比如基督教的祈祷,中国的祭祀,就会使人心里时常保持在那个状态。如果能够始终把心态保持在那个状态,就不需要拜,这个时候,命运就是在自己手上的。而这个心里状态,正是儒家和道家说的,需要日常的修炼。基督教的修炼,重点其实也是日常的每件事情,如果抓不住这点,就是假的信徒。佛教如果在家,修行手段主要也是日常,如果出家,专门修法门的话,日常倒是会少一些,但是目的是一样的。所以,重点就是要知道,锻炼的手段是日常的生活,锻炼的目的是让心在时时刻刻保持在那个状态。知道了这两点,拜不拜根本就不重要。
拜神该算是一种延续至今封建迷信活动同时也是种心理寄托的载体吧●文化习俗的代际传递潮汕人信仰佛祖和观音菩萨去霉运求保佑代际传递仍然生生不息给人们心理寄托拓展↪◤感恩的情怀◤祈福的信仰有求必应群体暗示◤仪式感可以提高幸福感◤利用信仰来左右超我道德束缚的畏惧◤..............#拜神有什么用?★潮汕不可遗忘的文化遗产↪可以带给人们幸福感和寄托↪.........尊重差异理解个性祝好!ZQ
1首先这体现出人们对新年的期望,同时也体现了家人的关心。再者,拜神也只是一种传达信仰的媒介,祈求的那些愿望,是为了心安,只要心安,其实有没有用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2拜神一定程度上创造出一片热闹,和熙的景象,附和过年气氛3然而拜神始终不是科学的,透露着我国仍然有着迷信风气的这样一个信息但拜神不能被禁止(也不可能,因为禁止了就使得某些烟香工厂倒闭,导致事业,也引起部分公民的发对,因为这也是他们精神的一种寄托,有点想宗教的存在意义一样,所以有那么多人拜神)就算是抛弃也需要一个过程,要抛弃的话就需要宣传科学知识,加强教育,是科学观点深入人心其实我觉得不应该抛弃,而应该是简化拜神程序,使其成为带有1和2含义的一种行为表达方式,只要心中是科学的,拜与不拜也不是个问题了(其实很多发达国家也保留一些类似的方式)所以拜神并不存在什么有没有用的问题,只不过是为了心安,为了精神的一种寄托。
对于神的概念,我还想多说几句。我们不是要成为神,而且无限接近神,我们成不了神,没人能成为神。神的概念是抽象的,是理想的,绝对的,不是现实的概念。和中国的天,道,佛教的涅槃是一个概念。就比如,没人能成为天,成为道,成为涅槃。也比如,没有现实的圆或直线,能成为绝对的圆或者直线。康德说过类似的话,说人类总是追求形而上,就像追求从地上走到天上一样,以为只要到很远的地平线,走到天和地想接的地平线,就能走到天上。但实际上不是,等你走到原来地平线的位置,现在的地平线又会后退到更远的地方,人类永远不可能走到地平线。基督教的神,是上帝,上帝这个概念和天和道是一样的,我们翻译过来是神。而我们说的神,是指像佛陀一样,有很大能力的一个生物,或者和我们不一样的生物。孔子家语里面,控制回答宰我的话里,说了人死后往下走的是鬼,往上走的是神,鬼神充斥在天地间,但我们看不见。提出了鬼神的存在,但没有进一步说。后来我们一般说的神,就是有超能力的,在佛教里面对应的概念是天人,道教里面对应的概念是仙(道教和道家不是一样的)。
这是一种风俗习惯。以前拜神有用,现在你就是神,所以,拜你自己即可。你要成为你的神。
有人确实很虔诚,大部分人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万一有用呢?

那么多人追捧成功学,所谓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
4回答 · 2025.07.11 19:10:18爱不爱一个人,跟给不给对方一个名分有没有直接关系?
5回答 · 2025.07.09 21:10:19为了自己的小家而与原生家庭保持距离,有错吗?
1回答 · 2025.07.07 17:45:53
分享一条觉得不错的回答,快来看看吧~
打开壹心理APP查看更多内容
4000万人在这里获得专业帮助
分享一条觉得不错的回答,快来看看吧~
4000万人在这里获得专业帮助